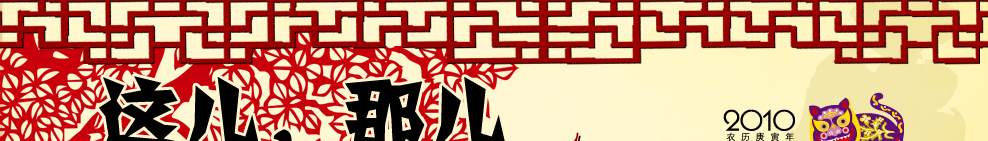田野上空流动着白茫茫的雾,这是30年前乡间的腊月,年关将近的村庄。
“娃,快点回家量衣服,裁缝到家了。”白雾中,传来母亲的声音。快过年了,村庄里弥漫着喜气,与这腊月的大雾交织升腾在山梁上。那时每到春节,村子里的人,都要请裁缝到家里制作过年的新衣。
过年的新衣,对一个常年拖着鼻涕在乡间泥土里打滚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大的诱惑力啊。平常的日子,我穿着母亲从别人家拿回的破烂衣服,做梦也想添件新衣。一个乡间少年的梦想,只有到过年才会实现。每到年关,母亲就会背着一个背篼,怀里手帕里包着供应的布票,赶到乡场上去买布料。母亲把买来的布料小心翼翼藏在柜子里,等乡里裁缝来家制作过年的新衣。
我10岁那年的腊月,身材矮小的裁缝来到我家,母亲赶紧燃起柴火,在锅里为裁缝煮上两个荷包蛋。灶膛里腾起的烟雾,把母亲呛得咳嗽起来,但那火光把母亲的脸膛映得彤红。裁缝在一旁吃了荷包蛋,开始拿起一把木尺为我们全家人比量衣服的尺寸。我长得瘦小,用的布料不多,母亲总是笑着说,娃,快点长高啊。那时过年的布料,都是千篇一律的蓝色咔叽布。
裁缝用了两天时间,把全家人的衣服赶制了出来。该轮到母亲为我们试新衣了,我脱下脏兮兮的衣服,把崭新的衣服飞快地穿在了身上,一溜烟跑了出去,一路欢笑蹦跳着跑到了村子里,我要向小伙伴们炫耀一下我的新衣服。母亲在后面喘着气追赶我,娃,娃,快点脱下来,等过年了穿。
我在母亲的催促声中不情愿的把新衣服脱了下来。我抱着土墙边的门梁,望着夕阳沉入大山那边,盼望着新年的到来。
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吃完团年饭,母亲升起火盆,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聊。山梁上的风,把木门咿咿呀呀地掀开了,母亲说,这是来报新春之喜的风啊。半夜,父亲的鼾声响起,想起就要穿新衣了,我兴奋得没了睡意。
大年初一早晨,我吃完母亲做的红糖汤圆,换上了过年的新衣,我和哥哥冲到院子里大喊大叫。伙伴们也早已经在院里聚集了,相互看着身上的新衣,暗中比试着谁的衣服好看。我们一群小伙伴,冲上了山梁开始玩捉迷藏的游戏。
我悄悄爬到一棵桐树上藏了起来。一个小伙伴眼尖,发现我后大叫了起来,我一个趔趄,从树上栽落下来,一个枝桠把我的新衣“噗”地一声划烂了。我呜呜大哭着回家,抓住母亲的衣襟要新衣服。哥哥随后追回了家,见我哭着向母亲要新衣服,他突然把自己的新衣服脱下,走到我身边给我换上了他的衣服。
我穿着哥哥显得长了一点的衣服,笑出了声,还是哥哥好。而我的哥哥,他又穿上了打满补丁的衣服。后来,母亲把我那件划破了的衣服缝好后,给了哥哥穿,他穿在身上有些短,有点滑稽。
30年的时光过去了,那年春节的新衣,却一直根植在我的记忆深处。我的哥哥,在20岁那年患白血病离去了。而今的日子,新衣服随时可以穿,但心里流淌的幸福,为什么没有那时候深?我多想找回那时春节对一件新衣服的盼望,小小的梦想,可以开花的那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