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啊,恨不得咬你一口!——再观再听莫言
莫言获“诺奖”过去一周多了,看到好多媒体关于他的采访,发现还有好多地方没有涉及。我8年4次采访他,静下心来仔细听听他的录音,受益匪浅。随手作了些记录。

莫言提笔写给大众日报记者逄春阶:“高粱之美,呼吸而领会者,唯我与春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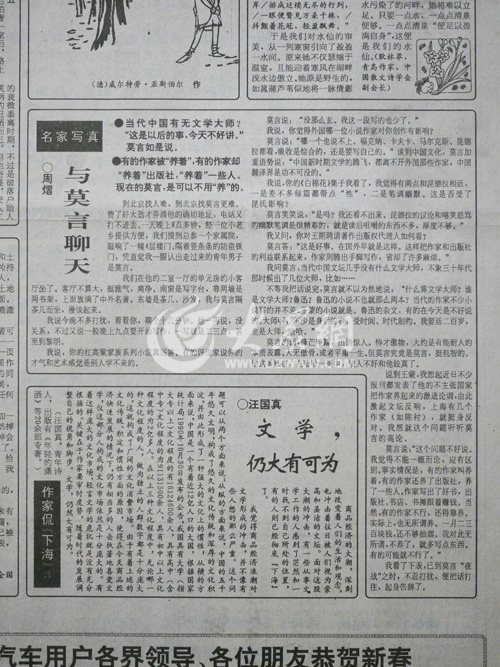
媒体以前报道过的有关莫言的文章

“国字”号文学杂志《十月》发表过莫言的文章《天堂蒜薹之歌》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故乡啊,恨不得咬你一口!
——再观再听莫言
大众日报记者 逄春阶
莫言获“诺奖”过去一周多了,看到好多媒体关于他的采访,发现还有好多地方没有涉及。我8年4次采访他,静下心来仔细听听他的录音,受益匪浅。随手作了些记录。
从时间洪流里淘洗“故乡”精华
走进莫言的故乡,看到的是平常的景物。但走进他营造的小说“高密东北乡”,则仿佛碰触到了他的肌肤,清晰嗅到了他的气息,抚摸到了他的血脉,倾听到了他的心跳。
我记起毕加索对画家塞尚的评价,塞尚画的静物苹果,毕加索研究发现:“塞尚并没有真正地去画苹果,他画的是这些圆形上的空间的重量。”就苹果画苹果,就不是艺术家了。我们也可以说,莫言并没有真正地去写高密东北乡,如果老老实实写,那是新闻报道。他写的是高密东北乡所承载的重量。莫言写得越淋漓尽致,离常人眼中的故乡就越远,但离心灵就越近,离文学也越近。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王德威先生在论文《原乡神话的追逐者》中,这样说莫言:“原乡与探史这两种欲望在莫言的小说中相互并列冲击。自特定的空间中追寻历史的痕迹,从时间的洪流里淘洗‘故乡’的精华,莫言的胆识用心,首先引人注目。他的故乡也因之成为反映中国现代史的新辐辏点,提供我们特殊的角度,省思一些熟悉的历史问题。”
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有段著名的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我套用鲁迅的话,写给莫言:“高粱之美,遍被沃野,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莫言而已。”莫言看了,笑一笑,提笔写道:“高粱之美,呼吸而领会者,唯我与春阶也。”我说,不敢,不敢。莫言说,高粱之美,我们永远也领会不完,这是期望。但现在高粱是越来越少了。但美在心中。
四次靠近莫言,我有点儿理解了他。莫言像块石头,是有重量的石头,是有棱有角的石头。可以在路边,可以在溪旁,可以在山巅,也可以在大厦的底座上。它沉默。沉默是它的生存方式。其实,石头是会说话的,因为把话藏得太深了,好像没说。莫言不说话,他用文学表达对故乡的爱和恨。故乡啊,恨不得咬你一口!那是另一种爱。
他心灵受过内伤
莫言是受过内伤的人。他的眼神中始终有一种忧郁存在,我能深切地体会到。那是让人灼痛的眼神。
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这样的成分在社会上,在极左的那个年代,往往是被边缘化的。别人家的孩子,可以读初中,可以当兵,可以入党。但莫言要获得,却十分艰难。
他受到的伤害,是心灵上的,是自卑,是压抑,是委屈,这个内伤,看不见,但是深入骨髓,比外伤更痛苦,也更难“治疗”,正是因为他的“内伤”,让他关注比他还要软弱的人,关注比他还要被边缘化的人,他为他们而伤心,而流泪。他用笔为他们呐喊。用笔“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
莫言说:“我的父亲非常严肃,非常方正,在我们村子里口碑非常好,现在也是这样。解放时 在我们村子里是大队会计,大队会计是可以脱产的,因此大队会计是可以不下地劳动的,天天在办公室里计算,我们村里没有能担任大队会计的知识分子,我父亲就当了。但因为我家是中农,他感觉到自己根不红,苗不正,所以要好好表现,他都是晚上算账,白天下地劳动,就是这样,他还受到村书记、领导干部的辱骂、训斥,他的心情很不好。再加上每天搞运动,今天‘四清’啦,明天‘文革’啦,你有没有经济问题呀,你有没有政治问题呀。我的大爷爷是老中医,是个地主,他的儿子是从青岛跑到台湾去的,也就是说,我父亲的社会关系也不清白,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父亲很谨慎小心,在外面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在外面受了气,回家自然也没有好脸色,所以我们一直很怕父亲,一直躲着他。”
青少年时期莫言用了两个“非常”:“非常痛苦,非常苦闷。”这些内伤不流血,但是持久地痛。“因为看不到希望!向往外面的世界,什么时候能跳出这个地方呢?到工厂里去,到城市里去,去当兵,上大学,但是很渺茫。当时上大学不用考试,像我们这种人也轮不到,当兵也轮不到,因为我们家虽然是中农,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村子里有那么多贫农,那么多干部的孩子,所以我从18岁开始每年参加体检,到了第四年,终于成为了落网之鱼,混进了军队。为什么说混呢?因为每年冬天都要挖水利工地,村子里的人都去水利工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在棉花加工厂里做工人了,像我们这一类青年可以就地体检、就地报名。所以当村子里的民兵连长在水利工地里挖河的时候,我在工厂里报名体检,然后跑掉了。”
做梦都在逃离故乡
到了部队以后读书多了,吃的也多了,星期六星期天可以休息了,但是对前途依然感觉很渺茫。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1976年2月份,一路上还要批斗,而莫言所在的单位尽管只有16个人,但没有干部编制,没有编制怎么提干呢,这样的单位,每天都打架。他刚刚燃起的希望又有破灭的危险。
当时,莫言出来的目的,就是想提干。提拔军官以后就可以离开农村了,不遭别人白眼了。转业以后就可以安排干部了,军官每月52块钱,一步登天,可以改变命运。
莫言做梦都在逃离故乡。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这个时候莫言在部队开始崭露头角。“因为我是中学生,所以他们给我报名,要我去参加郑州技术学院的考试,学计算机终端专业,就是学计算机维修的,我一听真是百感交集,这么好的机会,但实际上我小学都没毕业。数理化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我以为得五分之二,但是把这个说穿了,机会也就没了,于是我说让我试试,然后我开始学习,让我大哥把数学语文书一大包都寄过来了,白天站岗,晚上在储藏室里学习,到附近的中学去请教,总算把初中高中的数学顺了一遍,语文基本上放弃了,化学初中的第一册看了一下,物理看了一两册,这个时候,北京的上级单位忽然来电话说不用考了,没有名额了。我听了之后又很矛盾,一是费了很多劲,结果连考的机会都没有,二是暗暗高兴我终于不用去出丑了。”
这时候掀起了部队学文化的热潮,领导就说:管谟业(莫言)学了这么久,就由你来教吧。“业余时间让我讲数学,上级机关来视察,听我讲了一堂课,三角函数,政委是大学毕业生,一听,就问我:小管,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没上大学,中学都没上完,他说:你讲得很好啊。我心里说,知道你来听课我就背会了四道例题,第五道我就不会算了。他留意我了,然后几天之后把我调到北京去了,去了训练大队,但是后来下了文件说不允许士兵直接提干,然后就又搁浅了。我只有在那里熬着,正好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第五系下放到了某个单位,急需政治教员,他们就问我能不能教政治,我说试试看。因为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机会,教员有编制,我当时是保密员、图书管理员,还烧锅炉。政治教员,什么都不会呀,就死背硬记,整整一个暑假,在我们家旁边的空房子里使劲背书,村子里的人说这人当兵当出神经病了来了,整天在那里吆喝,南腔北调的。后来,开学以后,上了讲台以后就这么讲,同时,我开始试着写小说。”
为什么想起写小说,因为莫言觉得提干无望,还不如捣鼓点别的。当时刘心武的《班主任》已经发表,引起轰动。
于是,一个在村子里、在兵营里循规蹈矩的人,小心翼翼,惶恐地喘着气,没有了叛逆的激情,甚至丧失了怀疑的能力,像被剪掉翅膀的飞鸟一样的莫言,终于找到了自由的天空,接上了被剪掉的翅膀……
30年前不知有“诺奖”
1981年10月,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莲池》上发表了。这时候,他还不知道马尔克斯,更不知道有个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说,真正第一次接触马尔克斯是1982年的秋天,他去北京,单位让买点书去补充图书馆,他跑到北京的新华书店买了五六十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选》。
为什么选它呢?莫言说:“因为当时我一翻书,看到介绍说这个人是刚获得诺贝尔奖的拉丁美洲作家,非常独特。当时自己真不知道诺贝尔奖是怎么回事?就感觉是个大奖。买了这本书回来,说实话,看不进去。因为马尔克斯的书还是很难读的,当时我还是传统阅读,读的都是现实主义作品,都是红色经典,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读出来没兴趣,它里面没有故事,也没有很生动的人物形象。”
1983年9月,《莲池》第五期又发表了莫言的新作《民间音乐》,这篇小说风格独特,显示出了莫言的怪才,他一改过去的传统写法,而致力于营造某种意象。不久,这篇小说得到了独具慧眼的老作家孙犁的赞许。“孙犁写了一篇评论,后来我剪下来贴到本子上。”
孙犁的赞许,对莫言是莫大的鼓励。莫言说:“我这篇东西,故意使小说时代感淡薄,增添神秘朦胧甚至是荒诞的气氛,目的就是让读者不要用传统的的审美观念来看待我的人物……我那时才真正折服拉美爆炸文学,对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了高度认同,认为必须用动荡不安的语言,反传统的形式来形成自己的风格。”
1984年,他又接触了福克纳,他的探索走上了快车道……
理论读多了反而处处雕琢
莫言有特别高产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那时,《人民文学》《十月》《收获》等“国字”号文学杂志轮番轰炸。长篇、中篇、短篇,《红高粱》这些中篇,一个星期就写完。洋洋洒洒,汹涌澎湃,若决江河,沛然莫能御。
“那时候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再加上时间紧张,没有时间去认真想,初创时期一切都是新鲜的,它的许多方面是稚嫩的,有明显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另外一些方面是不可重复的,那种锐气,那种自由洒脱,那种胆大妄为、天马行空,现在无法达到了。现在让我写《红高粱》,肯定是另外一部作品。”莫言说。
莫言的创作经验,正应验了哲学家维柯的观点。维柯认为,人们的创造主要表现在诗性思维方面,先有诗人,然后才有哲学家。创造性往往与想象、野性、冲动和勇气结合在一起,而完善时常与理智、文雅、谨慎和遵循规范相联系。
莫言完全认可这个观点,他说:“作家的风格、创作是和他的整个生活密切相关的,随着创作经验的增加,别的地方反而可能不好。当时写《红高粱》的时候没有理论,就感觉应该这样写,觉得挺好,后来理论读多了反而处处雕琢,这个地方搞点象征,那个地方搞点寄托,出来之后反而一看就很匠气。换句话说,理论多了写书严谨,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没有才气,没有理论写出来的是天籁,就像歌手,去了音乐学院,唱得很标准,但是没有天籁,村里面拉出一个小孩让他放开喉咙唱,那就是天籁了。”
可以写得不好,但是不想重复
莫言说,写了三十几年,节奏放慢了。一开始的时候写的多,一年几十篇,后来几年越来越少,对自己要求严格了,写的多了,容易重复的可能性更大。我的标准是可以写得不好,但是不想重复。写的多了以后,总会有局限的。
最难的是否定自己。像长篇小说《娃》一样,2005年本来想写完的,写了5万字,写不动了。就感到突然无法继续了,人物不明确了,主人公该怎么发展,面目模糊了,不知道她究竟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莫言选择了放下。开始写另外一部长篇《生死疲劳》,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就感到特别顺,所以用43天就写完了40多万字的初稿,又过了两年,重新把《蛙》的废稿拿出来写,一下子感觉明白了,又是势如破竹。
《蛙》,让莫言等待了两年。他说:“说是等待,其实脑子一刻都没闲着,经常会想到这部小说,你在生活之中遇到的事件突然会联想到小说上去。比如《生死疲劳》也是因为结构问题进行不动了,后来我去承德的庙里,看到关于六道轮回的壁画,一下子感觉到脑子敞亮了。
莫言已经57岁,正处在创作的高峰期。但莫言是清醒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高峰,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吧,我希望自己能够东山再起,再翻一番。要有这种野心和这种愿望,要不怎么活下去呢?”
“我今年春天写的几个短篇还放着呢”
接近莫言的人,知道莫言内心其实很不轻松。有一个莫言的老朋友跟我说,获“诺奖”的那个时刻,其实莫言是百感交集。记者问他,他微笑着,回答自如,但是内心是苦的,他绝对想到了悲苦的童年和创作的艰辛。
莫言的痛苦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他说过:“写不出来,就是煎熬啊,煎熬就是没有好样子啊,抽烟啊,散步啊,转圈啊,抓耳挠腮啊,有时候也干点别的,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不要硬写啊,看看电视,看看杂书。”
一些人,创作可能心急。但我发现莫言不急。他是真不急,很淡定。他说:“不急,但是不愉快,一本书的相对顺利的写作当中,其实每天都一样,今天写了2000字,感觉不顺,明天这一段可能很有感觉,一下写了8000字,而且感觉每一次都很漂亮。经常会有这样子。”
记得路遥写完百万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把笔狠狠地扔到窗外去,然后痛哭失声。而莫言说:“在一个长篇划上一个句号的时候,那很轻松啊,跟农民锄地一样,锄到头了,直起腰来,劳动之后的愉悦。”
当然莫言自己也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很急,恨不得今天晚上写完了,明天就能发表,现在慢慢沉淀下来了,能够放着。“我今年春天写的几个短篇还放着呢”
【相关新闻】
【相关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