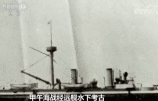在第二届中华国学论坛上的演讲(香港)
全球语境中的中华文化
许嘉璐
这次论坛以“中华文化与香港”为题,是很有意义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有助于对整个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共同体的认识,而且对香港未来的和谐与繁荣也有着巨大的意义。今天我们聚集在香港,当然重在对有关学理的研究——即探究中华文化和香港文化本体的内在本质、规律、沿革、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前景展望。我认为,时至今日,这种种思考需要现代世界的视域并且要有关注地球和70亿众生的胸怀。
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范式正处在又一次转向过程中 世界已经经历过了几次文化范式的转向。约略言之,希伯来宗教和希腊-罗马哲学结合,开启了西方的中世纪;后来,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结束了人们所说的黑暗时代,迎来了“理性”地追求真理的工业化的“现代”;现在则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技术信息化、社会碎片化、价值物质化的“后现代”。就在这第三次,也就是最近一次转向的同时,学术领域关于“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的思考与争辩热热闹闹,至今未绝。有关上述概念的界定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在有些方面则是众口一词的,这就是:时代转向了,“现代”留给人类的社会遗产背离了,甚或可以说是背叛了启蒙时代“理性”的承诺——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世界目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却正在走向危险的深渊。人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人类面临的危险度如何以及如何才是人类生存之路的不同见解而已。半个月前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登了新加坡的约恩·厄尔斯特伦题为《一个可怕的想法:全球性30年战争》的一篇文章。作者针对当前中东的乱局提出自己的担忧和分析。他说: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的30年战争,是“一个陷入困惑的欧洲谁有权定义伦理、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野蛮争斗,而“当今世界决定性的力量因素是形成观念的能力:定义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是与非、可与不可、当与不当。换句话说,形成一个基于价值观、吸引多数人的制度——占领自己定义的道德高地!”至于与这一思潮完全相反的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结论,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连他自己也已动摇了,究其原因,恐怕不仅仅是由美国爆发,继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由此引出的种种社会冲突;核心的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模范的美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定义观念的能力。
就在这时,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中国,和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一样,越过了欧洲14世纪之后那段艰苦的探索、思考、论证和实践过程,一下子跨进了“现代”的最后一班车;接着,工业化尚未完成,就糊里糊涂地被挟裹着进入了“后现代”。例如发达国家所遭遇的种种灾难在内地几乎一样不少。11天前,《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公布了内地社会心态存在的10大病症:依次是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暴戾狂躁、网络依赖、自虐心态。依我看,这10大病症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列为众病之首的“信仰缺失”是问题的根本。信仰缺失,安详心态、和谐生活和伦理道德何从谈起!
在此之前,中国文化经历过与欧洲不同的转向。如果我们暂且不论由殷商进入周代、文化在此定型和后来儒释道自身转折与新生的叙事(虽然我们从中可以受到文化生存发展的重要启示),中国文化近代的巨大转向,一次是20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结果是思想的大解放,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大转型,帝制结束,开启了对共和、独立的艰难探索里程。这一转向也给后来留下了文化领域的许多负面后果。大陆的改革开放,是又一次转向。这次与古代和近代转向之不同,即在已经不是基本上局限于华夏之族界域内(虽然此前的事件也受着外部事件的启迪和影响),而是几乎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在经济以令世界瞠目的速度发展的同时,中国文化也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节拍跳起舞来。社会差距拉大、环境迅速恶化、人生价值扭曲、社会伦理缺失、奢靡贪婪成性同时而至。但是,自最近一次世纪之交前后开始,“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形成了巨大的思潮,而且势头越来越大。这一思潮的特点,用大卫·昂莱的话说就是:“认可后现代,重估现代,回收利用前现代。”
我把这种世界的和中国的情况比喻为“赛车现象”:西方,首先是欧洲那辆车起跑,接着是北美的车紧随其后,不久北美的车超越了欧洲的车;中国车启动很晚,但车型较新,迅速地跟上来。前面的车转弯,后面的车跑到那里也必须转弯;前面的车所经过的颠簸处,后车躲不过;前车在某处侧翻,后车如不减速或采取应对措施,必然也要翻车。大家只有时间之差,却没有命运之异。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脆弱不堪和远非完美的发明”(大卫·莱昂)这说明,“西方的途径,就是说欧洲和北美的文化,不能再被当作标准和典范了。”
现在说到香港。如果用世界和中国文化转向的事实比照香港文化的历史,是否可以说,在祖国内地经历第一次转向时,香港已经基本接纳了欧洲文化,从此无意中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窗口、中欧文化对话、相融的试验场。换言之,香港在被殖民的条件下早于内地实现了“现代化”,具备了“现代性”。我之所以说在“在被殖民的条件下”,是因为“现代”所允诺的“民主”与“平等”,在回归祖国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并没有在香港兑现;但是“现代性”的其他方面几乎都逐步实现了,尤其是社会层面和价值伦理领域。“现代化”本来就是双刃剑。到目前为止,包括香港在内的大中国全境,都在既享受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成果,也被这柄剑的另一面割伤,而且伤口不小,疼痛不轻。
所幸,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早已在亿万民众的心底形成了文化基因。以往从西方来的文化冲击势头凶猛,国人曾经阻拦甚至抗击过;后来虽然接受了宗教、技术、管理和艺术,但是这种接受是“中国式”的,即在不违背中国人原有礼仪、风俗、习惯情况下的接受,也就是在不去除中华文化基因的条件下吸收西方于己有益的元素。香港先走了一步,至今不但儒释道三教共处并荣,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兼容,一些民间信仰,如关公、妈祖、土地、黄大仙等,也遍布全岛。按照西方神学家的说法,这是天启神教、自然神教、圣哲信仰(儒家)和巫觋信仰(占卜、看相、求签)并存于一体;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仍是香港人民的重要节日;“叹早茶”,是原汁原味江南习惯,如果在家里喝茶,喝法基本上是传统的,与喝咖啡相辅相成。这些都和内地并无二致。
正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基因如此牢固,所以内地近年来,尤其是进入这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回收利用前现代”已经成为从城乡公众到学者,到国家领导人,共同关心并参与的事情,而且这三类人渐渐趋向彼此相应与配合。只不过这种“回收”是直接回到轴心时代本民族的智慧巨人孔子、老子、孟子以及虽是外来却已经本土化了的佛陀那里,重新温习并审视他们的教导,寻其根本,汰其适合农耕和帝制时代,但已不适应现代的东西。例如对拜祭祖宗、先师、烈士蔚然成风,而采用的仪轨却大量吸收了欧美的;再如据对20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涌现出1600多家旨在传播传统文化的书院/讲堂/学堂,既有公办的,也有民间举办的;又如,许多企业,已经把营造企业文化作为重要事项,做得红红火火;还如在山东许多地方,“乡村儒学”——学者走进村镇,为村民讲述传统文化和本地乡贤、历史,颇受欢迎,民风也在悄悄地变化。如此等等,都说明人们普遍感到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做人处世的“伦理、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最适合自己;一味追逐利润和财富,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幸福。最近,北京卫视每天播放一档名为“寻找老街坊”的真人真事节目,非常受市民的欢迎。节目表现的是,已经住进宽敞楼宇,但邻里间冷漠、生疏、绝缘且彼此防范,因而感到孤独失落,于是想找回温情、平静、和谐的过去。由此看来,谁最有权“定义”人们应该怎样生活?是广大民众自己;谁最有能力“定义”道德标准?是现在依然还没有中断的祖父母或更早的前辈所留下的社会风尚。
面对着纷繁复杂、波涛汹涌的世界,人类将走向哪里?中华民族出路何在?众所周知,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曾经兴起了探讨人类共同伦理的潮流,一批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许多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借着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多元化、文化多样性学术之风,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所没有顾及到的“不同文明对话”和“构建人类共同伦理”的倡议和行动。不同文明对话是方式,是通道,是过程,构建人类共同伦理、实现地球和平是目的,是应对残酷的现实、消弭战争屠杀的远景。
哈贝马斯并不去否定“现代性”,认为现代性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他在认真研究当代思想演变状况后提出了“公共交往理性”、“主体间性”等一系列概念,为的是把启蒙运动旗帜上所标榜的“理性”进行改造(而不是“改换”),使人类走出困境。他的“公共交往理性”和启蒙时代的“理性”可谓截然相对。例如,不是提倡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成功,而是主张推己及人寻求彼此理解;不是一味竞争零和,而是努力商谈协作。
哈贝马斯的论著以语言艰涩著称,而与他几乎同龄的同胞孔汉思(又译汉斯·昆),则尽量使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孔汉思在长期研究世界所有“伟大的宗教”的基础上,开始为构建人类共同伦理呼吁奔走。他认为,在儒学、佛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宗教伦理中具有十分相近的要求;如果各个文明真诚对话,使共同伦理形成约束的力量,世界就可以获得和平和友爱。经他和同道者的努力,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上通过了《世界共同伦理》的决议,2001年联合国发布了《通往未来之路》(杰出人士小组报告:《跨越分裂,文明间对话,联合国报告》)。“构建共同伦理”一时间形成了欧洲学界的热潮。现在,虽然这一讨论的热度由于种种原因已呈减退之势,但他们开辟道路的影响仍在,当年那批学者功不可没。
但是,无论是哈贝马斯、孔汉思,还是与他们并肩奋斗的许多伙伴,都没有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所理想的回到前现代观念或发挥现代性的潜力,其关键,即人类共同伦理在各个文明世界如何内化为人们和社会的礼俗习惯、自发要求?也就是他们没有明确地把理想的世界伦理境界与个人道德修养的境界结合起来。在这点上,他们的思维进路有些近乎后现代主义。
有感于此,我在今年5月21日的尼山论坛上重新拾起“构建人类共同伦理”的话题,随后9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对此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令我高兴的是,每一次都得到各国许多学者的呼应。
我的想法是,由中国学者发起,接续“人类共同伦理”的探讨和呼吁。 三十年来,欧洲学者和神学家们的经验与成果将是接续者从事这一事业的基础和出发点。和前此的浪潮有所差异的是,我们应该更加强调不同文明的真正平等、相互尊重、真诚交流;由生活在不同文明语境中的学者讲述对本文明的反思与展望和对他方文化的感受;同时,还要积极向人们介绍不同文明内在不断提升、与“他方文化”交往的经验。显然,在这个论域中,中国学者和神学家们自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力求有所贡献,而在过往的三十年中,这方面显然是令人遗憾的。
说到这里,我的发言就该结束了。那么,就让我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再回到这次会议的主题“中华传统文化与香港”上来,其实这也是我发言的主旨。有了上面所讲内容的基础,我的结论就很简单了:整个中国,包括香港,祖祖辈辈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都在经受着“现代性”的“不完美性”的毁损,只不过各处表现形式和受害程度不一而已;人类的和地球的危机在内地和香港的头顶上徘徊着。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起“回收”历代贤哲的教诲,挽救社会,挽救民族;同时,还要一起和世界各国的智者加强沟通,为建构人类的共同伦理并使之在公众中传播、影响政府决策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